李勇:“史学史是思想史”沉思

“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系列研究Ⅱ:《史林》“笔谈: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
“史学史是思想史”,并非套用西哲柯林武德的箴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或者从中引伸,因为史学史原本就是思想的结果,只不过因为柯林武德对史学的潜思,提出上述那句箴言,使得”史学史是思想史”这个命题,变得尤其外化和引人注目了。就中国学者而言,史学史研究领域的先行者在处理史学史和思想史的关系上有何追求,又受到学界怎样的质疑,如何从形而上和研究实践角度去认识这个问题,实在值得做细致的分析。
一、先行者的开拓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史学史的著述要作为文化专史去做,具体写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其后,中国学界撰写史学史特别是中国史学史著作,在相当长时期内却多做成书目提要,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忽视了史学中的思想问题,这一定不是梁任公的本意。新中国建立后,一些史学史研究的先行者们提出,史学史要关注思想要素。
早在1961年,耿淡如在《学术月刊》第10期发表《什么是史学史》,主张:“强调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对各种唯心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对资产阶级伪科学的胜利”,“分析历史家、历史学派在思想领域内的斗争”,“应注意到其他科学领域的成绩与思潮”。须知,注意其他科学领域的成绩与思潮,是20世纪初以来新史学的普遍主张;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对各种唯心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对资产阶级伪科学的胜利,是那个时代的学术精神或者风气;耿淡如这样主张原本也不奇怪,但是他突出了“主义”“思想”“思潮”要素,则彰显其变革求新的思考,那就是要对以往书目提要式史学史著作加以完善或纠偏。
白寿彝在1964年2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指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首先要阐明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是什么?在他看来,它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历史的观点与反动、落后、武断、非历史观点的斗争。因此,把五四前后这些思想斗争加以区别,并联系起来加以研究,“ 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重要的任务”。白寿彝的观点跟耿淡如一样是那个时代使然,不过也突出了思想要素。两人作为新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和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奠基者,在这个问题上,其主张出奇地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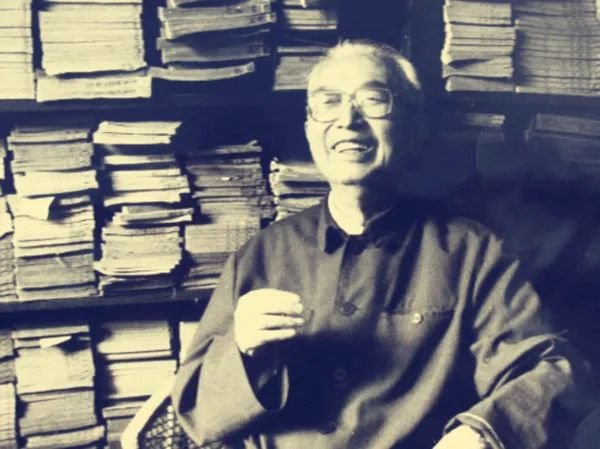
白寿彝(1909-2000),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吕振羽看到白寿彝的文章后,写出《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一些问题》,其中称:史学史是历史学中专门史研究的一种,“某些历史著作所包含的唯物主义观点和朴素辩证法思想,是在这个基础上与哲学史的一个圆圈一个圆圈相适应的”,因此,“从以往的历史著作中,指出其所包含唯物主义观点、朴素辩证法观点及其圆圈式的发展过程,察知其如何为历史唯物主义准备条件,或以之来丰富历史唯物主义,是有重要意义的”。其后学桂遵义论史学史研究道:史学思想“是史学的灵魂”,由于无论哪一个史家,哪一个史学派别,都有一定的思想作指导;因此,“研究史学史,通过对各个时代、各个学派的和史家的史学思想形成和演变的研究,探讨其历史学说的阶级属性、特点与发展规律”。他还说,有些人尽管不是史学家,没有留下历史巨著,但他们的各种历史观点,对后世史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应作为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对他们的史学思想予以历史评价”。
史学史学科的奠基者,当然不限于耿淡如、白寿彝等人,这里只是借助典型予以说明而已。一言以蔽之,1949 年以后史学史研究的先行者们,在史学史研究方面,其见解比以往有了新突破;他们的主张及其实施,往“史学史是思想史”这个命题所指涉的目标,迈出重大一步。
先行者的主张在后人那里得以延续和实施。在1985年的史学史研究座谈会上,吴怀祺批评以往史学史著作“忽视对中国史学史上的各种历史观点和史家的史学思想的探讨”。1996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国史学思想史》,2005年又由黄山书社出版他主编的十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张广智在回顾这一过程时,认为吴怀祺“此见卓识”,在自己主著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西方史学史》里,他有这样的设想:“研究西方史学史,应研究历代西方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它包括史家对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历史观),也包括对历史学自身的认识(狭义的史学理论);特别要研究历代重要的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因为他们往往以其高远的史学思想或奠基一个史学流派(如兰克),或创立一种史学新范型(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足以影响几代人,乃至在一个长时段中对史学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本教材确实按照其设想做到了。
上述主张还在其他具体著述中得到落实。例如,张广智主编的6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瞿林东主编的3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7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 ,于沛主编的6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陈其泰主编的5卷本《中国历史编纂学史》,胡逢祥等著3卷本《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等,无不关注社会思潮对史学的影响,无不突出史学思想的重要性。
二、“雷戈之声”的意味
就在上述学界思想高歌猛进的过程中,有论者提出不同意见,例如雷戈、鞠健等,发表《史学史与思想史新论》,对上述史学史著作的范型提出批评,姑名之为“雷戈之声”。
雷戈在文章中,不同意柯林武德的把思想看成高于历史的本体,认为在历史层面,思想就不再完全属于自身,即思想不再是本体;因为面对历史本体,任何东西都不再是本体。用他的话说,就是“历史本体高于一切本体。历史本体高于一切被称之为本体的东西。......毫无疑问,历史肯定要大于思想史。......不要把历史简化为思想史”。他把历史作为最终、最大、最高的本体。在雷戈看来,历史学的存在意味着思想的存在,意味着对历史的思考仍在继续, “史学作为思想,它对历史所作的思考并不仅仅是思想中的某一部分,而且是思想的全部”。他的言辞尽管拗口,无外乎是说史学是思想,又在思考思想,可以推论的是,思想是史学反思的对象。他这两点意见,避免了思想先于一切、大于一切、高于一切的逻辑设定,或者说避免了唯心主义;重申以往学界的历史无所不包、史学无所不容的信念。这些还都是学界的主流观点。

雷戈,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什么是思想史、史学史?这是雷戈的文章不能不回答的问题。
关于什么是思想史,雷戈说:“思想史有其特定的内涵。首先,它不是人们习惯上所说的那种如同哲学史、文化史之类的专门史性质的‘思想史’,它不是专门研究历史上所出现的各种思想的‘思想史’;其次,它不是柯林武德所指称的那种作为历史过程本身的‘思想史’。”显然,他反对从梁启超到雷戈发文那个时候的学界把思想史看成是一种专门史的主张和做法;也反对柯林武德的历史过程意义上的思想史。他提出了其新的看法,就是,“一切思想都是历史,一切思想史都是史学史”。
关于什么是史学史,与柯林武德和中国史学史研究先行者的看法都不同,雷戈以为:“史学史同样不是专门史意义上的‘史学史’,即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指历史学的历史本身,而非各种各样的‘史学史研究’。”2他把史学史界定为史学发展本身,不是后人反思后产生的学术成果形态的史学史。
这里涉及思想史与史学史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文已及,雷戈说“一切思想史都是史学史”,他还说过“史学史只能是思想史”,“史学史就是思想史”。至此雷戈还没显露对于先行者的根本性的批评意见。等谈及如何写史学史时,批评之声变得凌厉了。
他理论的前提是,思想史一方面是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创造出来的,也是普通人创造出来的;普通人以自己平凡的方式认真地思考着历史,从而使得知识范型的史学史和思想史具有了一个广阔的现实生活背景。其合理推论是,“史学史和思想史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和思想家的历史,而且也是普通人的历史”。这就意味着,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和著述,要把知识精英和普通百姓及其创造过程和结果统统包括进去。
对于史学史著作如何处理历史著作与思想的关系,雷戈认为,把史学史研究做成思想史研究,并不是简单地要求在研究史学史时突出或侧重于史学思想这方面,比如历史观和历史理论的内容,以至于把史学史写成史学思想史;而是从本质上讲,史学史的实际状态和思想史的实际状态完全相同,都是在思考历史的过程中成其为自己本身的,“这就要求我们只考虑实际意义上的史学史和思想史之关系,而不必煞费苦心地考虑专门史性质的史学史和思想史都有哪些特性和内容”。他的意见可以简化为,反对专门史意义上的史学史写作,不必考虑专门史意义上的史学史的特性和内容;而是考虑实际意义上的史学史和思想史之关系。前半部分语义清晰明确,后半部分语焉不详,但无论如何,都意味着对于学界研究史学史突出史学思想的主张和做法感到不满意。
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据其文字表述,可以归纳为:第一,“既不要把史学史写得同思想史一模一样,又不要把史学史写成是思想史内容的一部分。因为这两种做法都着眼于专门史的格式”。第二,“必须把史学史放到思想史的背景下来写,写出史学史与思想史的辩证互动关系。总之,要把史学史写出思想史的韵味”。
“雷戈之声”要表达的是,时至今日的史学史著述,都还没有突破专门史的窠臼,没有关注普通人的史学观念,没有写出史学史和思想史的辩证互动关系。
三、合理性与限度的沉思
“史学史是思想史”这一提法,有其合理性。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人的创造行为受思想、精神、意志和观念等的支配,思想、精神、意志和观念等是同一个范畴意义,因此可以说,历史始终是思想的产物。在现象上,历史,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意义上的历史、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联意义上的历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乃至一个一个具体人的类化为抽象的人所创造的,所改变的。人创造或者改变历史,是通过思想和行为来实现的。人的思想和行为,都会物化为文献和实物,知识体系中所谓的“史料”,其实就是这些文献和实物经过时间洗刷后的残留。实质上,在思想和行为之间,行为是思想来源的中介,思想是行为的驱动力,说到底所有历史文献和实物,始终都是思想的产物。简言之,一切的历史或者历史的一切,都是思想的产物。
历史学是研究历史的学问,是人对历史的反思;作为一定时间和空间中的现象,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一种历史存在;历史著作是人对历史的反思结果的表达,呈现为知识的形态,既是直接思想的一种,历史学是以一定体例所具现的成果,又是思想的产物。
历史学必须借助史料,而史料是思想的产物;研究历史必须借助思想方法和技术方法,而技术方法凝聚着思想的魔力,思想方法中的范畴、理论体系和逻辑终点,是自名为思想的;研究历史势必与其他研究者发生认识的同与异,其中的附和、补充、延伸,或者分歧、交锋和反驳,都是思想过程;历史研究者要把见解表达出来,无论是说还是写,或者使用融媒体,这个表达所借助的声音和形象符号都是人的杰作。简言之,一切历史研究,就是在反思历史,都是思想过程和本身。
史学史著述反思史学,作为历史存在,更是思想的产物。史学史,为史学之史,作为一定时间和空间中的现象,与生俱来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一种历史存在。史学史基本内容,要写史学家的成长与著述,史学家成长本身就是接受各种知识的过程,换言之是在各种思想中选择的过程,其著述就是反思历史,就是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意志物化为史著的过程。史学史要写史学家的历史观,历史观是史学思想最形而上的内容。史学史离不开对史著的阅读、阐释,离不开赞同与争鸣,这些阅读、阐释、赞成或争鸣的过程也是思想的过程。史学史要写史学家著作的史料价值、编纂体例,史料价值反映的是对后世征引者与阐释者的思想引导、激励、冲突和融合的意义,编纂体例是史学家写作的形式和规范,是史学家根据思想表达需要而涉及的形式和规范。史学史要写史家、史著,对后人的影响,那就是史著中蕴含的史学家的思想对于他人和后人的影响。史学史是一种知识,所有知识都属于思想,史学史是反思史学的产物,当然就是思想史。
当然,为避免最终走向唯心主义,可以继续的思路是,历史、史学、史学史,尽管是思想的产物,然而,创造历史、历史学、史学史的那些思想、精神、意志和观念等,却是要以客观条件为前提,没有那些客观条件,就无所谓之思想、精神、意志和观念等。
要之,“史学史是思想史”这一提法的合理性在于,史学史研究的对象中,史学家是思想者,史著是思想结晶,其地位和影响是思想的传承与流变;史学史研究各环节,包括文本阅读与意义揭示、论证逻辑的构建、写作体裁和凡例的选择,无一不是思想本身及其产物。故史学史原本就是思想史。
“史学史是思想史”这一提法,当有其限度,不容忽视。
其实,学界早已有人意识到史学史与哲学思想史的区别。例如,耿淡如认为,史学史是属于思想意识领域内的历史,但不是一般叙述历史哲学的或社会思想的历史,因此,史学史应和历史哲学与社会思想史有联系也有差别,它通过具体历史著作或历史上争论的问题来说明历史家或历史学派的进步或反动的思想意识。史学史在叙述思想方面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历史家或历史学派对整个历史过程或个别事件所采的解释方法与立场观点,因而估计它们的作用。它不是一系列理论与名词的堆积”。后来,桂遵义主张研究史学思想时,应注意把它同一般哲学思想区别开来。他认为,哲学思想指的是世界观,是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认识的总和;史学思想主要是指史学家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其历史发展过程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哲学思想是指总的指导思想,而史学思想是从属一定哲学思想的,并受其所支配和制约的。因此,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这些意见,对于认识”史学史是思想史“的限度是有启发的。至今,关于这个问题有些方面还值得进一步思考。总的想法是,先行者的追求是可贵的探索,值得继承;“雷戈之声”也不可充耳不闻。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把道术史、史学史、社会科学史、自然科学史当成学术思想史的分支,尽管他没有具体论说社会科学史、自然科学史的做法;又把学术思想史与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文学史、美术史并列,作为文化专史,尽管他也没具体论说文学史、美术史如何做。非常可贵的是,他把史学史作为专史,也就是今天所谓专门史,把史学史看作学术思想史,这些被新中国史学史研究先行者继承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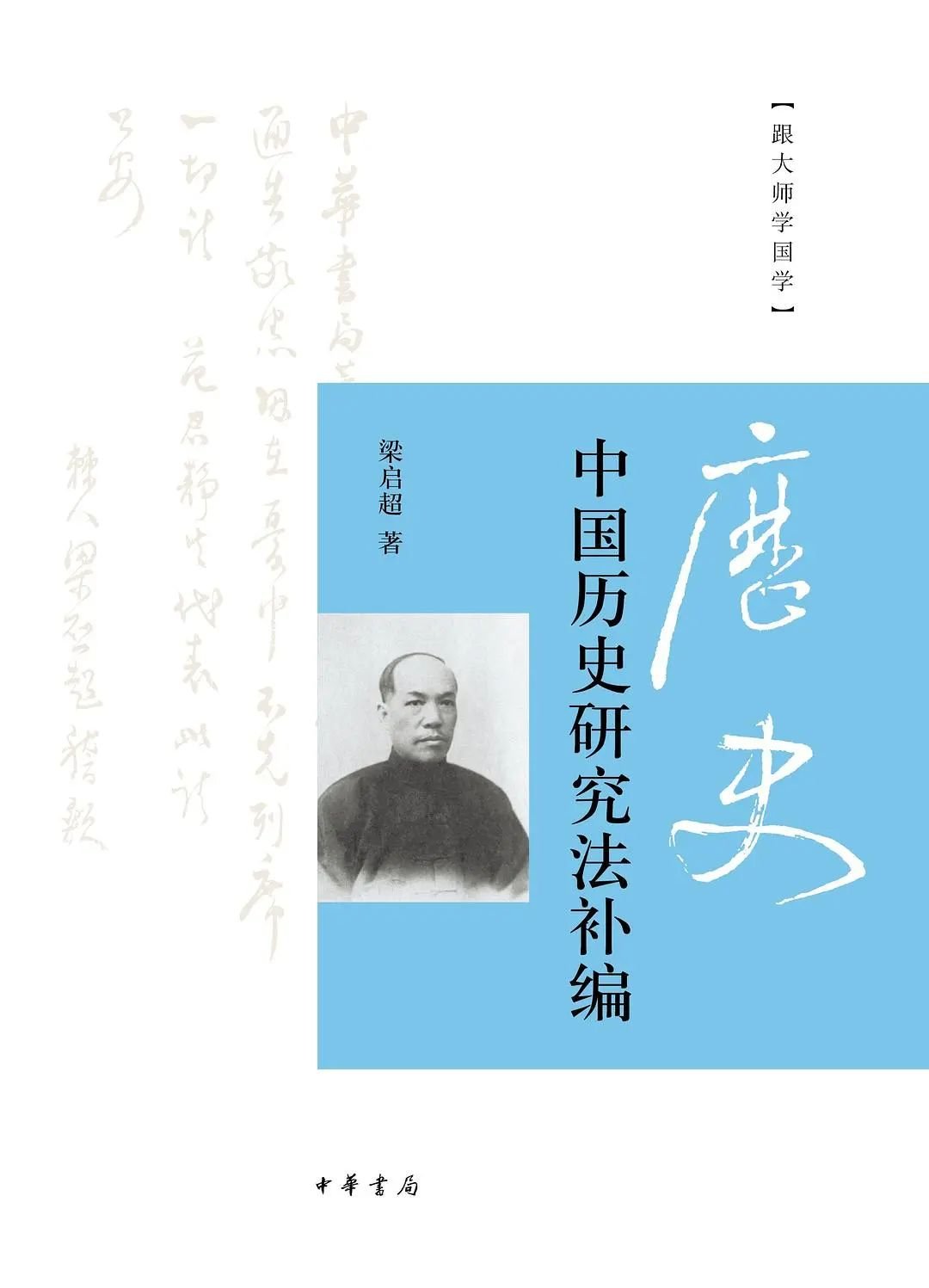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批评者雷戈,赞同史学史的思想史做法,但是反对把史学史做成专门史、做成知识精英的思想史。“雷戈之声“有些提法是有道理的,例如,他把历史作为最终、最大、最高的本体;主张史思想是史学反思的对象;要把史学史写出思想史的韵味;关注普通人的历史认识。其实,他这些想法也差不多是学界过去的做法和未来的追求。史学史和思想史一方面有交叉,另一方面又有分离,这恐怕是雷戈没有意识到的,或者虽意识到但未作论述。这个问题说到底是“史学史是思想史”的限度问题。作为概念,“史学史”“思想史”的词源,目前一时难以明晰;学术史上之所以区分这两个概念,有其学理逻辑。其学理逻辑的基础是:第一,史学史的重点是历史著作及其相关问题,思想史的重点是思想著述及其相关问题,这就决定两种是分途的,或者各自进行的。第二,在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实践中,史学史难以包含所有的思想,思想史又不可能囊括所有历史著作,遑论普通人的历史认识,这就不得不认可史学史和思想史的并存。第三,史学史研究中,要介绍史料留存情况,叙述史学家搜集、整理史料的情况,这些是现有的思想史写作范式所无法越俎代庖的。
然而,由于它们具有共同的反思的特性,因而史学可以反思思想,思想亦可以反思史学,这就决定史学史少不了思想,思想史里少不了历史著作。同时,历史上有不少人是百科全书性的学者,是史学家同时还是经学家、文学家等,在研究这些学人时就一定会出现其史学家、思想者线索的交织乃至纠结。这就决定史学史和思想史许多时候是交叉重合的。
至于怎样做史学史,以下几条还是可以站得住脚的,可以视为对“雷戈之声”的回应,视为“史学史是思想史”在实践上的限度:
从学术史研究可操作角度说,史学史还是处理为专门史为好。无论把思想史纳入史学史,还是把史学史纳入思想史,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无论如何,理论玄思是一码事,实际研究是另一码事;只能说在进行史学史研究时,不忘它与思想史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此而已。
研究史学史,当考察史家所处时代的思想环境,考察史著所涉人物的那个时代的思想环境;考察史学家的思想,除了像有论者所说的史家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观念)外,1还要注意其关于经济、政治和伦理等方面的思想。
研究历史观和史学思想,包括研究对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的认识,就史料而言,扩大其范围,从知识精英所创造的著作之外摭取思想材料;就角度而言,揭示不同史学家在思想上的认同与交锋,同一个史学家在不同时期的变化。
总之,从反思的特性上说,史学史就是思想史;史学史反思史学,思想史反思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思想。从研究的实践上说,先行者的专门史、重视历史观和史学思想的做法值得肯定和继承,同时思想史研究的路数也值得参考和吸纳,是史学史研究再出发的一个表征。不仅研究中国史学史如此,研究西方史学史亦如此。

作者简介:李勇,淮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