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啯匪”和“会匪”:哥老会起源的新思考(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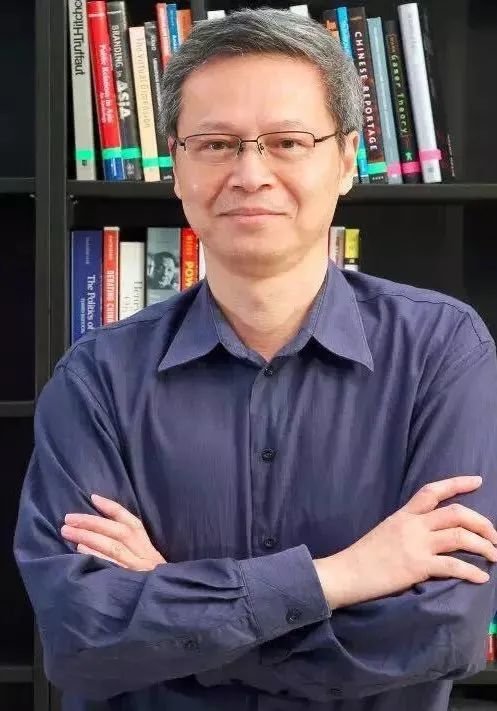
作者简介
王笛,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紫江讲座教授,同时兼任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生特邀研究员。
摘要
在中国秘密社会研究中,学者几乎都认为哥老会是由啯噜演化而来。但是从啯噜到哥老会的演变轨迹,很难建立起逻辑的和有说服力的联系。在清朝的档案中,啯噜和哥老会的区分是非常清楚的,啯噜被称为“啯匪”,从乾隆初期便已经存在了;哥老会被称为“会匪”,在同治以后才开始流行。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学者,应该说都是有一定的史料根据的,这些史料主要来自清代官方或者官员对啯噜和哥老会的描述,但是几乎都是只言片语。如此就认为哥老会来自啯噜,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接受了清官方的一种对边缘人群的话语表达。而那些表达不一定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其在很大程度上是歧视、愤恨、污蔑的结果,或者就是为镇压这些反叛者寻找理由。由于对哥老会的镇压无力,而且这个组织还有扩大的趋势,因此污名化或许是一种策略,或者是利用道听途说的信息进行的武断的推测。
关键词
啯噜;哥老会;流民;李调元;严如熤
七、三省边界的啯噜
地处川陕边境的太平厅,原来设县,后来由于军事上的重要性,升为直隶厅。太平厅“所管地极辽阔,周遭一千七八百里,近厅之数十里,官渡湾一带平原水田为产谷乡,余则多未开老林”。厅所辖城口,距厅三百七十里,“四面高山峻岭,中间一线溪流”。这一带“极其幽深,俗称八百里城口”,所以为“啯匪”“教匪”提供了“往往伏匿”的地方。[52]
保宁府“长材深菁,动辄数百里”,成为“啯教各匪,易于伏匿”的好地方,因此“防检不可少疏”。这里所说的保宁府,就是阆中,为古巴子国,距成都六百二十里,为川北重镇。往东去太平,往西去梓橦,往南去西充,往北经广元去陕西宁羌,“栈道千里”。剑阁为四川的北门,“水流湍激,山势嵯峨,故一路号称天险”。从保宁府往东北四百里为通江县,与陕西定远厅接界;往北三百里为南江县,与陕西宁羌褒城、南郑接界。通江和南江两县“均无城郭,县治毁于贼”,但是这个地区有不少“大石寨”,这些寨子“倚山阻水,环绕十数里,天险可守”。在这些大石寨中,“百姓屯聚其间”。甚至也有官员驻扎,以便于就近管理,即严如熤所称的“官弁即侨居其间就近抚驭”。严的描述很生动真实,他说“蜀山陡起陡落,山麓稍平,有溪泉浇溉,便成水田”,所以通江和南江也产稻谷。严把山区的自然景观,描述得准确到位。[53]
这些流民和啯噜藏在山里,就像有了根据地一样,可以长期生存,政府和军队对他们也无可奈何。所以严如熤才说:“清野之策可行之山外,而不能行于山内。”也就是说,在大山之内实施所谓“坚壁清野”的策略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可供利用的资源很多,可以自给自足。在溪河的两岸,早麦三月已有成熟,低山的麦子五月熟,高山的麦子则六七月始熟。包谷种在平原山沟者,六月底可以摘食,低山八九月熟,高山在十月熟。在高山的地方,甚至干脆就不收割苞谷,让其就在大自然中,“包谷既熟其穗倒垂,经历霜雪则粒更坚实”。由于山民无仓库收贮粮食,往往只好“旋摘旋食”。当遇到雨水多、发生涝灾的时候,那里的乡民就依靠高山的作物;如果是发生旱灾,就依靠低山的收成,即所谓的“岁潦则望高山之收岁,旱则资低山之熟”。[54]
严如熤还揭示了啯噜逼迫乡民入伙的办法。这些“贼匪”如果在山中遇到年轻人,则把他们抓去,“反缚,令负粮跟走”,逼迫他们“惘惘行山谷中十余日”。由于去乡已远,也不知道到了何处,已经没有了其他的选择,然后“渐释其缚,逼令刺杀所掳之人,以坚其心,不则谓无用转杀之矣”,就是说逼迫他们去杀人,要不就是被杀,这样才能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们干事。严还透露,他们喜欢“掳十数岁小孩,教以击刺”,就是从小训练他们打打杀杀。年纪稍大者,“号曰毛牯锥”;年纪再小者,“号曰马娃子”。因为他们“幼小无知”,以“杀人放火为顽戏,便捷轻锐如锥如马,故以为名”。[55]
在山里,也有交易集市,所以“山民贸易定期赴场”。也有的集市“开于无人烟之处”,被称为“荒场”,其实那些地方主要是交易山货。有时候正在交易的过程中,如果有“啯匪猝至”,管事的“场头”恐怕被抢劫,于是就各家收钱,交给“啯匪”以避祸。所以严如熤说,“场头恐其劫掠,敛钱相赠,所全者多未可遽以通盗绳也”,也就是说,不能把这个送钱给“啯匪”的人,以“通盗”的罪名来处罚。[56]严如熤在谈到这个地区的抢劫集团的时候,有时用“匪徒”,有时用“啯匪”,甚至“匪徒”也有红钱和黑钱的区别,更有毛牯锥、马娃子等等名目。
在山内的“各色痞徒”,也会去城市“闲游”,应该是去城市作案,统称为“闲打浪”。这些人在军队招募的时候,也会进去“充乡勇营”,所挣得的银钱“随手花消”。如果遇“啯匪”,则加入其中,“相从劫掠”;但是遇兵役追捕的时候,他们则站在兵役一边,“相帮搜捕”。真是身份多变,左右逢源,可以参与任何一方面。这个倒是透露了他们成为啯噜的一个途径,即:闲浪的人——乡勇——闲浪——啯噜——乡勇——流贼……他们这些人,“不事生业,总非善良”,也就是说没有固定的生计,“闲打浪既久,便成啯匪”。在严如熤看来,所谓“啯匪”,实际上就是白莲教和地方土匪,即“啯匪之聚即为教匪、流贼”。所以首先应该消灭无业游民,也就斩断其来源,“则盗贼自弭矣”。[57]
山中还有许多猎户,平时“专驱除虎狼”,他们都持有火枪。另外,各厂为了“防啯匪劫掠”,都备有“标客”和“拳勇”,都是有武功之人,称技击可以一当十。各州县也组织“民壮”与兵役“一体操演”。山内地方辽阔,虽然有汛兵,但是“偶有盗贼,文武措手无策”,也没有足够军力进行搜捕,“以致浸酿事端”。因此,严建议,根据山内县的大小,大县设一百四五十名,小县至少一百名,组织民壮“勤加操练”。每名每年口粮开支银十二两。[58]
八、坚壁清野
为了维持三省边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清政府也派了驻军镇守。定远设厅治,边防由定远负责,西乡游击营驻扎。诸要隘需要“时防山寇躏入”,也就是要“御贼当在门墙之外”。严守定远,则西乡“自可固圉也”,否则龙池坝、马家坝、箭杆山各险,“贼”可以到处“窜越”。因为定远十分贫瘠,所以“割西乡隶之”,这样厅县的事务办理起来便要容易一些。厅东北九十里的江口,为“南山扼要之区”,厅西的黑河一带,上接凤县,下通褒城、沔阳,西与甘肃毗连,“密林深谷,绵亘数百里,极为幽险,最宜防范”。黑河为凤县和沔阳管辖,设有铁炉川守备营。褒城的马道,相传为萧何追韩信处。由于是交通要道,所以驿站重要,依靠驿站聚集起来的人口,比县治还要多。留坝厅境“绝少水田”,但还是吸引了“川楚棚民转徙开垦”,这里的“土著十无一二”。由于人口复杂,流民为多,“五方杂处,易生事端”。[59]
为了加强三省边境的防御,清政府新派驻兵,即增加了“营汛”(或称“汛营”,凡驻扎在县及县以下地区的即为汛兵),“用资弹压”。新汛营的兵丁,许多“系降匪乡勇充当”。当被政府围剿之后,“伙党赴营投诚”。地方在招募乡勇、兵役的时候,也经常以那些“无籍可归者”为对象,因为担心他们在社会上游荡,“恐滋事端”,便把他们“收入营伍”。但是这些人“本非善良,杀人放火习惯成性”,所以进入军队以后,根本就不能“安守营规”。但是在军队里,比他们过去的境况要好多了,“口粮优厚,打仗有赏,杀贼有获,饮酒食肉,日日醉饱”。严如熤提出“边地兵饷有宜变通者”。在白莲教暴乱发生之前,山内的粮食非常便宜,也就是严所说的“绝贱”,大米每石价值不到白银一两。以后山内“连岁荒旱”,大米一石价常在三两以上,包谷一石也要二两多。粮食涨价后,老兵由于“在营日久,或薄有田产,或兼营生理”,家底稍微殷实一点,尚可“勉强支持”;而新兵则于饷银之外,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生计更难”。所以严提出各营每人按月发给米三斗,以及一定的盐菜,让兵役有基本的生活保障。[60]
根据严的说法,新兵“为山内患”,是因为兵有定额,在军事行动结束裁撤乡勇之后,一般应该“递送回籍”。但是他们所注籍贯“本非真实”,到籍后“并无亲族收留”,仍然到处流窜。有的则因为“在外日久无颜回里”,又中途逃回山里,企图再进入乡勇营。结果造成“已撤乡勇逼留山内者”,越来越多。他们无事时则“为闲打浪”,游荡“村寨墟场”。所以严指出,山内防范之策,以安抚流民“为第一要务”。流民在山里“开山作厂”,有了生计,各安其业,这样“奸徒亦不能以煽惑”。哪怕万一有人蠢蠢欲动,但是“好乱之奸民终不敌良民之多也”,也成不了大事。另外,山内的差役多由“客民”充当,差役是引起问题的源头,因为他们“遇棚民有事,敲骨吸髓,弁兵亦多附和为奸”。由于地方偏僻,山民“受其凌虐”却没有地方申冤。[61]
山内还有包揽诉讼的问题,“闾阎受累,实由于此”。严认为,四川和湖北的“民情”本来就“好事”,也就是不安稳,喜欢惹事,“加以光棍包揽教唆,鼠牙雀角便成讼端,差役手奉一票便为奇货可居”。哪怕是非常小的纠纷(也就是所谓“鼠牙雀角”)也可能引起诉讼,那些差役则滥用职权,用传票来获利,往往“将所唤之人羁押,中途客店店主串通一气,彼此分肥”。[62]
保甲本来是防备盗贼的制度,而在山内的各州县,则只可行之于城市,而不能行于村落。因为“棚民本无定居”,甚至一年内“迁徙数处”。甲长保正相距数里乃至数十里,根本不可能随时稽查。外省的流民入山以后,“多寄宿林岩”。所谓客店者,也不过是“贸易山货之小贩”而已。各县的边境距离县城达数百里,如果客店必须报告所住之客,每个月核对,也是十分繁复,照例造报,“仆仆道途,不胜其苦矣”。[63]
四川东、北各州县,靠近陕西者,距成都往往二千又几百里,而湖北的郧阳,距省府武昌则“更迢遥”。所以治理很难兼顾,如太平县的城口、洋县的华阳、安康县之砖坪(即岚皋)、平利县的镇坪,都是这种状况,下面所管辖的乡镇离县治都十分遥远。严如熤说,“坚壁清野均制寇良策”,但是地域太广,地势太复杂,所以“山内之野难清”。不过“坚壁”不失为“确有成效”的办法。当时官府中主张要发展“寨堡”,山民尽倚险结寨,平原之中亦挖壕作堡,牲畜粮米尽皆收藏其中。探有贼信,民归寨堡,凭险拒守。贼至无人可裹,无粮可掠,贼势自衰矣。寨堡之设是为了“固足保民”,这对于“剿贼”大有好处。因为那些“贼匪”在山谷中奔窜,官兵“尽力穷追”,但是相距也“总隔一二日程”,因为前面没有人“阻截”。如果修筑了“寨堡”,加上团练,就不怕他们“据险以拒”,大兵及时跟击,“鲜不获大胜者”。严如熤赞赏山民“质朴、劲勇、耐劳、习险”,这是平原地区的老百姓所不能相比的。如果在山内训练团练,则“贼匪畏之”。[64]
但是,当“贼匪滋事”的时候,官府中有人建议,由于这些雇佣的工人有可能“被贼裹诱”,所以应该“严行驱散”他们。但是严如熤认为,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凡开厂之商,必有赀本足以养活厂内之人,必有力量足以驱使厂内之人工作”。其实这些开厂的老板,更关心本地区的安全,所以“侦探贼踪,往往较官府为真”。另外,一般开厂的地方,都是选择那些“险峻可守之处”,他们还“结寨屯积粮食”,有能力维持稳定和自保。如果不准开厂,“则工作之人无资以生”,反而会增加“十万无业流民”,这些人“难保其不附从为乱”。所以严如熤建议是不作为,其实这种不作为,应该是非常好的作为,比那些激进的官员更懂得地方治理,即所谓“只当听其经营不可扰也”,这个“不可扰”就阐释了一个非常好的治理理念。[65]
严如熤提到“古人”的“平贼方略”是:“征调不如招募,招募不如团练。”但是严认为,应该两者兼顾,“相兼而行,则战守有资矣”。团练虽然属于民间自卫组织,但是“亦须官府激励,少为赀助”。如果地方有事,官员“量为调剂”,便可以“固境保民”。另外,供运能力也十分重要,各交通要道、各寨都要“预为储备”,当官兵临境之际,“必贼匪滋扰之时”,那么就需要设法供运,“防贼匪拦抢”。而那些担任供运之人,就尤当仔细斟酌,严如熤认为,“用家丁不如用差役,而用差役不如用绅士”。这是因为“家丁入山,行李先自累坠,路径不熟,闻贼胆怯,往往粮运不到,浮开运脚使费”。也就是说使用了家丁,钱花费了,但结果却不妙;差役要好一些,他们“路径熟悉,兼恐误差责惩”,但是如果没有人约束他们,确实“亦难得力”;绅士则不同,他们居住“寨堡之中,其心急欲官兵杀贼地方宁静,事虽公,而切己,办理较实心也”。所以地方官要依靠“绅士耆民”,先给他们发运营银两,物质转运及时,“决不敢误”。在这个问题上,要“官民一气”,因为两者是“休戚相关”。[66]
关于组织团练,过去总认为是劳命伤财的事情,严如熤却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当“贼匪”到处发展的时候,山内的州县不可能“处处用兵防守”。团练虽然“不足以当大贼”,但是防备小股的盗贼确实有用,即“声势既张,则小队贼匪亦不敢轻有窥伺”。因为“贼匪”在行动之前,必然先进行探视,如果发现无备,就会“乘虚而入”。但是地方有了团练,情况则大不一样。“团练既成,每月操练两次,不过费两日工夫,其余二十八日尽可力作”。也就是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并不需要花费多少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收效却十分明显,否则,如果没有团练,“则贼匪日日滋扰,地方光棍加以恐吓,百姓日藏山洞不敢耕种,其废时荒业为何如”。[67]
严如熤还具体讲述了在山内训练“团练之法”,各寨“寨勇”设寨长、寨副、大旗、小旗,以次分管。寨长心须“寨民公保”,若干个寨一起,要选一个能人充当“寨总”。当然,一定是选绅士中“有才干、为众所服者”。在靠近边境要隘之处,各寨要轮流派人“设卡守之”。当百姓分散耕种之时,为了防备“匪之突至”,各卡要派人于高山眺望,发现有“贼踪”,则放一炮示警,而“耕作之人尽皆收捡农具”;如果发现“贼向此路”来,则放二炮,人畜皆归寨堡内;如果“贼”已经接近,则放三炮,寨总领导各寨“尽整器械,集壮丁堵御”。另外发警报还要接力,就像烽火台一样,“前卡信炮既放,后卡闻声接放,顷刻之时数百里间咸知警备”。如果发生失误,如“贼至不放炮”,或者“非贼至放炮”,寨总要查出“禀官严惩”。[68]
他甚至对侦探也有提及,如果情报没有探明,就会误事。有的探卒敷衍公事,“往往于中途逗留数日,回则糊涂捏报”。所以各州县要准备“木戳”,也就是印章,一个侦探进入本境者,他的“探票”要得到“寨总戳记”。也就是说,一个侦探进入山区,还必须持一张“探票”,也就是执行公务的凭据。如果需要去邻省邻县,其所到的县,还需要“于票内加用印信,以杜道听途说之弊”。如果票内无戳记、印信的话,就“必加重惩”。[69]
严如熤甚至还考虑到了武器的问题。林中所产老毛竹,节密而坚柔有劲。“贼匪”把毛竹砍作长一丈七八尺,作为“茅杆”,前面加一个茅头,便是非常厉害的茅枪。他们在对抗官兵时,“千矛攒刺”。如果短兵相接时,很难接近,而且“前矛甫开,后矛已至”,一排接一排。在他们力量不敌官军的时候,则拔出矛头,弃杆轻装逃遁,“形同猿猱窜至他处”。到了新地方,又砍竹作杆,再做成茅枪。由于在密林之中,官军的火枪、弓箭也不是很有效,于是也用长矛,“彼此刺击”。所以时人说:“两鼠斗穴,将勇者胜信哉!”[70]在平原上,弓箭和火枪能射很远,十分得力,所以“贼匪”深知扬长避短,不肯轻易离开老林。嘉庆三年的盩厔之役,白莲教首领齐王氏“率贼匪数万人出山攻扑”,[71]前去镇压的清军血战不敌,“贼用马队直踏而前”。在关键时刻,山西千总崔雯率领“藤牌军二百名跳跃出迎”,结果敌方“马惊窜自相践踏”,这样才挽救了战局,营兵“鼓操继之,贼匪始退”。次日清军马队至,一皆当百,“贼死伤大半,逃遁入山,自是不敢轻窥”,所以平原“剿贼之师,弓矢、枪矛、藤牌均宜分队练习,不可偏废也”。[72]
九、啯噜的消弭
乾隆之后,档案中关于啯噜的记载明显减少。嘉庆十年,四川总督勒保奏查办啯噜事,仍然是老调重弹:“川省五方杂处,游手最多,往往结党成群,流荡滋事,日久即成啯匪。”根据蓬溪、射洪两县禀报,有“匪徒”李猴子等,“结盟拜把,纠夺人犯,纠众行窃”,各属先后拿获李猴子、李大武等31人,并有范老三、罗老四自行投首,“一并押解来省”。经审讯得到的口供,李猴子即“李良德等”,说明他用了若干化名。勒保称他“素行游荡,均非善类”,常在李应喜家中来往。嘉庆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李猴子和李应喜等闲谈,“起意结拜兄弟”,这样可以“有事彼此帮助,以免被人欺压”。李应喜等应允。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奏折提到了“结拜兄弟”。
口供称,李猴子逼令范老三、罗老四一同结拜,范老三等“无奈允从”,与王小二等共13人在柳树沱地方“沾香拜把”。因李猴子为人强横,众人即让李猴子居首,但是“并无歃血焚表情事”。这些人的名字,似乎暗示了他们在结拜中的位置:王小二、范老三、罗老四、李小五、苏小六、赵老八、王老九等。十一月二十四日,即结盟后第四天,王老九、李小五二人在柳树沱场“行窃”,刚好有差役在那里巡查,即将二人拿获。李猴子“因同伙被擒,起意夺回”,得到赵老八等支持。于是李猴子、苏小六等各拿凶器,乘将李小五等押解之时,“即追赶上前夺犯”,解差吴珊等不能抵御众人,李小五等被其夺去,但是“并未伤人”。在过去关于啯噜的事件中,多是官兵一来就逃散,而这个案子,头目不惜抢夺被捕弟兄。勒保奏称,李猴子各依“发司差人捕获罪人,聚至十人中途打夺,为首者斩监候律”。[73]
档案中关于啯噜的记录越来越少。道光二十二年(1842),浙江道监察御史朱监奏称:“川省啯匪虏人勒赎,并乡民众抗官。四川田地膏腴,……称地方无事,妄冀苟安一时,以此乡民各不聊生,多人入城躲避,亦有联结数十百家,聚为一团,互相保护。汉州等处,各聚八十团,推生员黄来璧为团长,制备枪械,以资堵御。达县则推冉姓为长,巴州则推苟姓为长,贼匪稍知畏避,而团内良莠不齐,亦有妄为非法者,团长倚峙人众,私相庇护,抗拒官长,不许传讯。且有以睚眦小怨,即捏指为匪徒,而擅加凌虐者。”[74]按照这个奏折的说法,“川省啯匪”在嘉庆年间白莲教叛乱时,“趁机裹挟,所到村镇,焚掠一空,至用兵十余年,糜饷数百万,地方始克平静”,其所形容的这个规模,怀疑是把白莲教的叛乱加在了啯噜的头上。到了道光年间,“党羽纵横,日甚一日”。如道光二十二年彭县一案,“闻有文武生员及差役人等,俱各与贼相通,虽拿获百余人,而为首系魏元宝,迄今实未获案”。朱监要求下旨饬四川总督,“凡啯匪盘踞地方,令该管员弁密相知会,不分畛域,四面堵拿。获案之日分别首从,立置重典,不得以驱逐出境,暂时相安,即为了事”。[75]
这个奏折透露了如下重要信息:一,为了抵抗啯噜,乡民大规模地组织在一起,甚至数十家、数百家,“互相保护”;二,乡民称自己的自卫组织为“团”,其头目也已经有了明确的名字,叫“团长”;三,乡民有了明确的自我保护的意识,而且为了保护自己的成员,不惜对抗国家权力,即“倚峙人众,私相庇护,抗拒官长,不许传讯”;四,这种社会组织不仅仅包括民众,而且还包括了“文武生员及差役人等”,其成员已经多元化。根据这些信息,倒让我想到了哥老会,如果来做一个大胆的推论的话,这些乡邻组织起来对抗啯噜的“团”,倒很可能就是哥老会的早期形态,是一种守望相助的组织,这和后来哥老会的发展、性质也是相吻合的。
在道光时期,啯噜从过去多发生在川省与他省的边界地带,似乎逐渐进入四川的内部,甚至成都平原。道光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四川总督宝兴上奏,“查川省啯匪,大为民害,缉匪实为要务”,称四川“先后拿获大股匪犯”,包括崇庆州等处及仁寿、合江、垫江、邻水等县,“强掠、轮奸、杀人各匪,并获抢夺滇省丝客案内匪犯等一百数十名,均经分别提解来省审办”,此外还有崇庆县等处“匪犯”杨老五等案45名。十月初,又“风闻”成都府属之金堂县、简州等处,“复有匪徒纪四帽顶等聚众滋扰,兵役掩拿则恃众抗拒”。在威远县,有“匪徒”拒捕之案,当即派城守营捕拿,但“该匪等已奔至汉州,沿途裹挟,已有数百人,驻扎合磐场,经汉州于十月初六日五鼓赴彼三面兜击,匪势猖獗,官兵众寡不敌”。“匪徒”约有二百余人占据觉华寺,后大量官兵到达,当时杀死五十余人,生擒七人,夺得大炮、排枪、长矛等件,“余匪四散逃遁”。头目“纪四帽顶”等皆被抓获。[76]
同治元年(1862),署四川布政使刘蓉在致郭嵩焘的信中说道:“蜀省生齿至繁,无业游民殆近百万,其稍驯者,则趋井厂、充桡夫以营衣食;桀骜犷悍之流,则当私枭,为啯匪,如所谓‘闲亡’、‘帽顶’、‘哥老会’、‘千字行’之属,不下一二十万人。”[77]刘蓉在另外一个场合又说:“哥老会其源盖发于蜀,根株最深,蔓延最广,盖青莲教之余孽,所谓红钱会者,其头目曰帽顶,总头目曰大帽顶,其最大者曰坐堂老帽。设有管事人员,各立名目,不可胜纪。入其会者给予牌符,转相煽诱,其能招聚百人者为百人头领,招千人者为千人头领,招万人者为万人头领,各立某山堂字号以区别之,如龙虎山忠义堂之类,自分支派,不相混淆,闻今且遮于天下妄分五旗,籍两湖、江西者为白旗,籍两粤闽浙者为黑旗,籍皖吴河南者为蓝旗,籍云贵、陕甘者为红旗,籍独四川者,为黄旗,尊其教之所自出也。”[78]刘蓉的这个叙述,反复被有关研究者所引用,其逻辑是,既然清官员刘蓉都说啯噜头目叫帽顶,哥老会首领也有叫帽顶的,所以传承关系就是铁板钉钉的了。但是刘蓉的两段话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他先是把“啯匪”与“闲亡”“帽顶”“哥老会”“千字行”都拉扯到一起,后来又说,哥老会又是从“红钱会”和“青莲会”而来。刘蓉在把哥老会与这些地方土匪组织拉扯到在一起的时候,实际是道听途说,没有经过仔细的考察。但是我们后来的研究者,却把他的这种道听途说、随意的甚至可以说是随心所欲的记录,作为了啯噜是哥老会前身的最重要的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严如熤说到了啯噜的“拜把”活动:“啯匪之在山内者,较教匪为劲悍”,他们往往隐藏于“未辟老林”之中。所谓的“未辟老林”,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原始森林”,他们在原始森林里“斫木架棚”,“操习技艺,各有徒长”。他们形成了一定的群体,所谓“什伯为群”,十个、几十个到百人的群体,“拜把之后不许擅散,有散去者辄追杀之”,就是不能退出,否则就不免有杀身之祸。[79]这种拜把活动,后来成为许多学者认为啯噜是哥老会来源的重要依据。但是根据啯噜的各种文献,虽然提到了结盟的问题,但是结盟在其活动中间所扮演的角色,和后来的哥老会是完全不同的。
在光绪六年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奏报中,也强调了啯噜“烧会结盟”的行为:“川省啯匪烧会结盟之风,甲及各省,年来严督各属,力行保甲,随时联合查拿,获办极多,稍微敛迹。”但是这年三月,营山县属柏林场,有外来“匪徒”一、二十人,持有军械,混入场内,经团民捕拿,“该匪胆敢拒捕,伤毙团民”。后该县拿获“杨大帽盖”,他带有枪械,因为店主不允留宿,“即持刀砍杀,将店主戳死,并开枪拒伤团丁十余人逃走”。该县还拿获蒲登柯等七名,经审讯,称李麻子“拜会充勇,趁机抢劫”。这里所谓“拜会充勇”应该是讲的两件事情,即结盟(“拜会”)和冒充乡勇(“充勇”)抢劫。太和镇拿获赵定国,系甘肃人,“搜出招勇印信三颗”,即交蓬溪县审办。[80]这个奏报透露了另外一个词汇“烧会”,以及四川“结盟之风,甲及各省”,也就是“结盟”成为“会”,还有“拜会”活动,其实就是入会的仪式,甚至有了“印信”。结拜、结盟在中国历史上的边缘人群中——包括政治的、宗教的、犯罪的,是非常普遍的行为,但是这却成为后来学者论证啯噜向哥老会过渡的主要依据。
十、哥老会是啯噜演化而来的吗?
对于哥老会起源于啯噜的论著很多,这里我集中讨论蔡少卿先生的观点,他是中国秘密社会研究的权威,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而且蔡先生提出这个观点比较早,后来的许多研究受他的影响很大。蔡少卿先生认为“哥老会发源于乾隆初年四川的啯噜会”,但是到嘉庆、道光年间,“由于南方天地会势力的北移,与川楚一带的白莲教啯噜党势力相会合”,它们之间经过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才形成了哥老会的组织名目”。同治、光绪年间,随着湘军等军伍的遣撤和破产劳动者无业游民队伍的激增,哥老会即勃然而兴。哥老会不是啯噜组织的简单重现,或名称的变异,而是“以啯噜为胚型”,吸收、融合了天地会、白莲教的某些特点,“在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定社会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无业游民组织”。蔡先生进一步论证从啯噜发展到哥老会的过程:就组织形态来说,哥老会与啯噜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异姓相约为兄弟、结盟拜把的组织;啯噜有红钱、黑钱两种,哥老会也有红帮、黑帮之分;啯噜头目曰帽顶,总头目曰大帽顶,最大者曰坐堂老帽,哥老会也有类似称呼。[81]
尽管蔡少卿先生认为哥老会来源于啯噜,但是同时他也看到了哥老会受到其他如天地会秘密社会组织甚至白莲教等的影响。也就是说,哥老会的形成有多种因素,但是它来源的主体仍然是啯噜。蔡先生把啯噜和哥老会的组织形态和活动进行比较,包括抢劫等,如他引用“天下第一伤心人”的《哥老会说》,“其党每于山隘及江湖港边泊船所在,谋劫客商,多遭惨害”。抢劫活动本来就是边缘人群的普遍行为,既不能说是啯噜、也不能说是哥老会的独有行为。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哥老会的抢劫是例外,而对啯噜来说,抢劫却是一个常态。
其实根据蔡先生的分析,啯噜和哥老会之间的不同也是很明显的。如啯噜一般不设“堂口”,而哥老会的组织系统,多设山堂香水;另外,哥老会内的开山仪式、会规条例以及暗号隐语等,都是啯噜所没有的;哥老会在组织和信仰等方面都具有天地会的特点。我认为,这些因素才是辨别它们关系的关键。所以蔡先生的结论,“啯噜出现在先,哥老会出现在后。显然,后者是从前者演变而来的”,[82]就和蔡先生所举出的两者重大的不同相冲突。
我同意蔡先生所说的哥老会与天地会、白莲教、湘军裁撤、社会矛盾加剧、游民增多等各种社会综合因素的关联,但是蔡先生所说的主要观点哥老会发源于“乾隆初年四川的啯噜会”,我认为是证据不足的。乾隆及以后时期的啯噜,说到底就是土匪的同义词,它根本就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组织,而是一群乌合之众,也就是邱仰文所定义的“伏以啯噜者,匪类之总名也”;也如李调元所称“啯噜,良民之蟊贼也”。在乾隆时期的四川,只要是土匪,那么就叫“啯噜”。正如四川总督福康安给乾隆皇帝所建议的:“啯匪字样本无意义,若留此名色,转难示儆,请于条例改为川省匪徒。恶名既已永除,匪迹自无蹈袭。”[83]按照福康安的说法,“啯噜”其实就是土匪的意思,就该还其本来的面目,通称为“川省匪徒”。今天我们不会把土匪作为一种严格意义的社会组织来看待,而简单地认为是抢劫团伙,或者是一种行当,是一种落草为寇的选择。他们从来没有像哥老会那样有自己严格的行为规范、内部规章、政治诉求等等这些成熟的组织要素。
我认为哥老会来源于啯噜缺乏依据,但是并不否认一些啯噜子加入了哥老会。哥老会本身的成员就是非常庞杂的,三教九流、各种社会背景的人都会加入哥老会的组织之中,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这个组织就是他们过去所属的团伙演化过来的。例如,资料中也频繁提到许多啯噜加入了白莲教,我们不会说啯噜是白莲教的前身;哥老会的黑话中有不少的词语借鉴于屠夫这个行业,但是我们不会据此就说哥老会的前身是屠宰业组织,主要成员是过去的杀猪匠,等等。其实同样的逻辑不仅是针对哥老会的起源,也可以用在对其他秘密社会组织起源的研究上。它们的成员可能来自各个行业,甚至各个阶层、各个地区等,无论这些成员过去有什么背景,他们的背景并不重新定性所参加的那个新组织。相反,他们成为那个组织的新的成员,被那个组织所定性。例如,一百个曾经的湘军士兵加入了哥老会,那么他们就是哥老会成员,我们绝不会说湘军是哥老会的前身。我想这个逻辑完全适合于讨论啯噜和哥老会的关系。另外,现今能够读到的官方文献,关于哥老会与啯噜关系的依据多是只言片语,并没有任何完整的叙事和细节以及逻辑的连接。而那些在档案中有详细记录的案例,却没有一项可以支持哥老会演变自啯噜的这个观点。[84]
最后我还想说明一点:本文中所使用的关于啯噜的资料,几乎都来自官方和官员的描述,完全没有啯噜自己的记录。他们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今天已经完全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所以,他们到底是国家权力的反抗者,或者是更复杂的结盟的团体,还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完全是由官方来定义的。当我们今天利用官方的记录来对啯噜进行描述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个先天的缺陷。作为历史的研究者,不能把清官方的话语或者话语霸权简单地接受。因此,清朝官员对当时的边缘人群和秘密社会组织的一些污名化的说法,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意识到这只是代表了官方对这个山区边缘人群的描述。同样,当官方和官员把哥老会等同于啯噜的时候,我们需要持更大的警惕。相对啯噜而言,哥老会却完全不同,他们能够留下大量的对自己历史的描述,哪怕其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传说、神话和历史糅合在一起,但是至少我们今天还能听见他们的声音。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声音,我们才能够把哥老会与啯噜的界限清晰地划分出来。
注释
[52]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14页。
[53]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16页。
[54]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8页。
[55]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30页。
[56]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30页。
[57]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32页。
[58]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34页。
[59]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5-6页。
[60]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32页。
[61]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33页。
[62]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37页。
[63]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34页。
[64]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41-42页。
[65]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9页。
[66]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37页。
[67]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36页。
[68]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44页。
[69]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44页。
[70]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45页。
[71]据严如熤主修《嘉庆汉中府志》卷32《拾遗》,则有“十余万人”。
[72]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45页。
[73]刘子扬、张莉编:《清廷查办秘密社会案》第1册,第444-445页。
[74]刘子扬、张莉编:《清廷查办秘密社会案》第1册,第445-446页。
[75]刘子扬、张莉编:《清廷查办秘密社会案》第1册,第445-446页。
[76]刘子扬、张莉编:《清廷查办秘密社会案》第1册,第446-447页。
[77]刘蓉:《复郭筠仙观察书》,《养晦堂文·诗集》卷6,光绪丁丑思贤讲舍本,第18页。
[78]刘蓉:《养晦堂文·诗集》卷8,第28页。
[79]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30页。
[80]刘子扬、张莉编:《清廷查办秘密社会案》第1册,第447-448页。
[81]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205-207页。
[82]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206-207页。
[83]刘子扬、张莉编:《清廷查办秘密社会案》第1册,第443页。
[84]关于啯噜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是在乾隆四十六年,我写了一篇长文《消失在崇山峻岭:1781年川鄂湘山区啯噜及清廷的围剿》(《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更全面地对啯噜及其活动进行了描述和讨论。
编辑:浅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