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季节》,中国改开历程中的一页痛史


五一档的影视剧市场,最火的莫过于由辛爽执导,范伟、秦昊、陈明昊领衔主演的《漫长的季节》。自4月22日甫一上线,就在豆瓣得到9.0的高分,随着剧情推进,分数越来越高,5月1日大结局之后,更是冲上不可思议的9.4分,远超春节档的热播电视剧《狂飙》。

如果说《狂飙》讲述的是一部黑社会的长成史,那么《漫长的季节》聚焦的则是改革开放历程中工人群体的一页痛史。
关于改革开放的历程,向来有两副面孔:
一副是以安徽小岗村(农村改革)、深珠汕厦四大特区(城市改革)为发端,由点及面、不断深入,积极向上、喜笑颜开的面孔。以往的主旋律文艺叙事多聚焦这一面,比如早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到近几年热播的《大江大河》《人世间》等。
另一副则是由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包括失地的农民、下岗的工人等弱势群体的泪水汇成的哭脸。只是因为这些群体缺乏话语权,这一面以往很少被人关注。而《漫长的季节》以一起18年前的碎尸悬案为引线,追忆并呈现了改革不为人所关注的另一面,引发大量亲历者的共鸣,进而收获到超出预期的口碑效应。
那么,这页痛史究竟有多痛?后来又是怎么翻片的?为什么不该被人们,尤其是年轻人遗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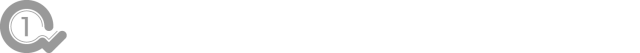
1949年以后大规模的就业难情况,大概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60年代中后期,此后全国便掀起了针对“老三届”“新三届”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该运动虽然裹挟着意识形态的因素,但很多学者都认为,它和50年代末以来一连串经济政策失误造成的城市就业压力有密切关系。只不过在当时,由于普遍的贫穷、严格的管制以及革命话语的鼓动,经济层面的因素并没有对社会产生太大的冲击。
真正的冲击发生在十年以后。随着知青的陆续返城,而国营单位又没有那么多岗位可以安置他们,导致城镇待业人口激增。一些人因为无事可干,整日游手好闲甚至聚众斗殴,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中国第一代的黑恶势力,就是在这个时期冒出来的。
多年以后,作家孔二狗将这段经历写成了小说《东北黑道风云往事》,一时爆红网络。当然,小说家笔下的故事都是经过美化的,而现实比这要残酷得多。据公安部统计,进入1980年代后,各地恶性治安案件频发。1980年,全国立案超过75万起,其中大案5万多起;1981年,立案89万起,其中大案6.7万起;1982年,立案74万起,其中大案6.4万起……这直接促成了1983年的严打。
今天的人谈起那次严打,聚焦点多放在诸如唐山菜刀队等黑恶团伙,或者朱国华、“二熊”等被正法的权势子弟身上,而对于其背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迟缓、就业供给侧不足等深层次问题,却很少留意。
相较于广大农村,中国的城市过去在“二元体制”下享有诸多特权,用农民的话讲,城市职工是“吃商品粮”的。当时像鞍钢这样的国营大厂,职工穿着厂服走在大街上各个都是昂首挺胸,满满的自豪感和优越感。
但这也带来了两个问题:
一方面,人人挤破头都想进国营大厂,而瞧不起刚刚萌芽的民营经济。比如《漫长的季节》中,工人劳模王响念兹在兹的就是将儿子王阳送进桦钢,哪怕彼时的桦钢已濒临倒闭,也不愿意他去夜总会挣每个月300块+小费的“高薪”。
但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晚于农村,当农村的乡镇企业已经办得热火朝天,城里却还是各种国有或集体单位一统天下的局面。尽管它们通过开设分厂、职工子女顶岗等方式,吸纳了一部分待业青年,但要想靠这些存量企业解决所有的就业问题,显然不可能。
记得90年代初有一部热播电视剧《孽债》,从孩子的眼光,讲述插队西双版纳的上海知青离婚返城后,子女从云南到上海寻找父母过程中品尝到的艰辛冷暖。但如果我们把视角切换到他们的父母,则又是另一番悲情叙事。不同于留在城里的兄弟姊妹,这些人在边疆、在农村吃了多年的苦,但回来后要工作没工作,要住房没住房。
好在严打的第二年,也就是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拉开。很多人靠着摆地摊、跑运输甚至各种“投机倒把”行为,攒下了第一桶金。反倒是像王响这样曾经手捧铁饭碗、受人尊敬、令人羡慕的国企职工,在几年后沦为了另一场失业潮的主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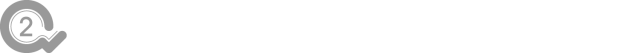
关于上世纪末国企改制的利弊得失,从学界到民间,至今仍存在不少争论。
一方面,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面对外企、民企的激烈竞争,国企体制僵化、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等问题越来越暴露出来。到1997年底,全国16784家大中型国有企业中,亏损的有6599家,亏损总额达到666亿元。光靠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或推广承包责任制,已无济于事,必须进行产权改革。
但另一方面,产权改革必然涉及员工的分流下岗,而大范围下岗潮所带来的改革阵痛,落到每个家庭头上,都是难以承受之重。数据显示,单是1995年到2002年,国有和集体企业就精简了6000多万名职工。套用北野武的话说,悲剧并不是下岗了6000多万人这一件事,而是下岗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6000多万次。

南方还算好,由于民营经济发达、外资企业众多,下岗人员的出路还算广,国企的接盘侠也多。
比如我妈她们家两代五口人工作的造纸厂,先是将我舅所在的车间连机器带员工卖给了一家德资企业,这部分人转制后收入不仅没降反而还涨了。而剩下的总厂部分,由于负担相对较轻,又有政府的背书,所以对富余职工采取“内退制”——通常比正常退休年龄提前五到十年,内退后每个月能从企业拿到几百块钱的“退休费”,而政府也针对这部分4050人员提供一些技能培训,帮助其再就业。
比较惨的是东北,一来这里国企工人数量多,二来民企、外企又少。一些年纪较轻或有一技之长的,下岗后纷纷选择南下,形成了第一波东北人南迁潮——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90年代东北人口净流出40.4万人。
但更多的家庭,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即使是像王响那样的熟练技工,也不得不留在原地。这部分人的境遇就相对悲惨许多。当时,诸如下岗工人冬天了没钱交取暖费在家挨冻,生病了没钱看在家等死,甚至丈夫骑着单车送妻子去KTV上班的报道比比皆是。
《漫长的季节》呈现的正是这部分人的心酸苦楚。据说剧中原有刘全力带着儿子接在维多利亚做陪酒女的李巧云下班一幕,记得那些年,每次跟大人去卡拉OK厅,他们唱得最多的一首便是刘欢的《从头再来》,曲调是高亢的,但歌声却很凄凉。一曲唱罢,总会伴随着一串对于社会、对于厂长的“祖安输出”。以至于后来黄宏因为在春晚小品里说了一句“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被全国的下岗工人足足骂了好几年。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被很多国人所批判的苏东国家剧变后采取的“休克疗法”,认为该法搞乱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让人民陷入贫穷。但某种意义上,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中国国企转制改革,也不啻为一场休克疗法。
但正如我们在东欧看到的,除了俄罗斯等少数几个国家,大部分国家采取“休克疗法”后的阵痛期只有短短几年,此后经济便开始复苏反弹。而中国的运气似乎比东欧还好,“国企三年脱困行动(1998-2000年)”结束后的2001年,中国便正式加入世贸组织,经济从此步入快车道,失业率也随之下降。
所以追剧时看到有评论说,龚彪如果不是因为黄丽茹而胖揍厂长宋玉坤,能熬过那几年不下岗,像他这样90年代的大学生,进入21世纪后一定能大展拳脚,前程似锦。这也是许多观众最同情龚彪,而不是死了妻儿的王响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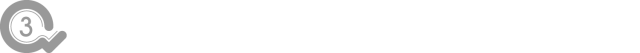
今天很多缺乏历史知识的年轻人喜欢骂资本家,觉得天底下所有的坏事都是资本家干的,不理解70、80后的人为啥会崇拜互联网最初的那批创业家。但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品尝过国企改革阵痛的人,想必都对那个年代的厂长有深刻印象。
名义上,厂长只是工厂的管理者,他们中也诞生过像张瑞敏、步鑫生等改革先锋,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时候,厂长握有比今天很多民营企业主更大的权力,却承担着更小的责任——
这两年由于经济不景气,很多民营企业主都吐槽“自己是在给员工打工”,而想当年,哪怕国企效益再差,厂长也只是打报告向政府求援,而在工人面前,依旧趾高气昂、说一不二。工人受了委屈,还无处去说理,不像现在,可以劳动仲裁,也可走司法程序。
这种权责不对等带来的腐败空间,在国企改制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那时候谁留下,谁下岗,往往就是厂长、工会主席等几个人说了算。甚至像《漫长的季节》中,龚彪因为黄丽茹的事打了厂长宋玉坤,后者便临时将他的名字加到下岗裁员名单中的情况,也不是没有。
更为恶劣的是,一些厂领导勾结外商、偷卖物资、中饱私囊、化公为私的情况屡屡发生,而像宋玉坤那样被法办的却寥寥无几。这些都在工人中间激起了广泛的愤慨,直到零几年的时候,还曾发生过吉林通钢集团工人抗议重组打死新任老总的重大事件。
正因为有过这些经历,很多人才会对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物资生活的大幅改善充满感激,对白手起家、不依靠权力获得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心生敬佩。《漫长的季节》结尾,年老的王响对年轻时的自己说的那句:“往前看,别回头”,很能代表那代人的人生观。
但是,这种进步主义的乐观情绪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像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这样一路单边向上高速发展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属于非常态。
当非常态回归到新常态,青年人失业率持续走高,我们有必要回头看,从历史中去寻找经验教训和解决方案。这也是《漫长的季节》收获比《大江大河》《人世间》等改革正剧更高评分的原因。
就像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所言:“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